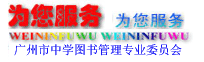广州教育学会中学图书管理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论文
过去二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和出版特点综述
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 唐黎明
过去二十年,我国的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令人鼓舞。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1.组织井然,规划有序
1.1建全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
1.1.1 定期召开会议
过去的二十年,经常召开各种有关古籍整理工作的会议。1990年底,新闻出版署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总结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经验,研究了问题,进一步组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92年5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为大会题词;宋平、李瑞环为大会发来贺信;全国十余家报纸对会议情况做了报导,盛况空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关怀,进一步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另外,学术界也举行了各种会议,共同切磋古籍整理的技艺。
1.1.2成立各种组织,定期出台各种规划
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利用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努力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1981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为古籍整理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目标。重新组建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任命李一氓为组长,于1981年召开古籍规划会议,讨论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2)》;1991年,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和“八五”计划》,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古籍整理计划,组织古籍研究、人才培养和出版工作;还有一些与古籍关系密切的专业部委,如:国家教委、农业部、中国地方志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工作委员会等,也相继成立了有关机构并制定了实施计划;1983年国家教委成立了以周林为主任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1984年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卫生部制订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计划整理686种医药古籍。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干预,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此项工作的有计划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和经济基础,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1.3 设立奖励项目
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颁奖大会于1992年3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37家出版社的117种优秀图书得到了国家级古籍图书奖荣誉。《甲骨文全集》等7种图书获得特别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15种图书获得一等奖,《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56种图书获得二等奖,《九章算术注释》等29种图书获得三等奖,《山左名贤遗书》等10种图书获得丛书奖;在首届“国家图书奖”获奖名单中,不泛古籍整理类图书存在。如:获得国家图书荣誉奖的有《中国历史地图集》、《永乐大典》、《大唐西域记校注》等。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的有《文心雕龙义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有这些都表明政府是极其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
1.2 成立研究出版机构,培养古籍整理人才
古籍整理研究,工程浩繁,学术性很强,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根据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由国家教委主持组建研究机构和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在80年代前期,在有基础、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陆续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的科研与教学机构。其中由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联系的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18个古籍研究所、一个研究中心、二个研究室和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大、上海师大四个古籍文献专业,共25家。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专职科研、教学人员有30余人,兼职人员290多人,形成了600多人的相对稳定的队伍。其中教授一百多人,副教授一百余人,博士生导师二十多人。此外,各省市属院校也成立了研究机构,目前,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与全国省属院校的64个古籍研究所(窒)建立了业务联系,并与教育系统以外的研究机构协作,从而在全国形成了100多个研究单位。千余名专家参与的古籍整理研究体系,使过去那种小规模的或个体分散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成为大规模、有领导、有规划的国家文化建设事业。
上述机构不仅是中国古籍研究整理的基地,而且也是培养古籍人才的中心。有4所大学的古籍文献专业已毕业的本科生就达400余人;各研究所和古籍文献专业培养的硕士研究生500余人,博士学位获得者100多人。同时,在全国数十所高校图书情报专业,还普遍开设了古籍整理课程,有的还招收了目录学、中国古籍文献学的研究生,为古籍整理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一般都分配到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教学单位、图书情报系统、出版社及与古籍整理研究有关的文化教育部门工作。经过实践锻炼,已有一批人成为教授、副教授。其中一些人已成为较有名气的青年学者。这说明中国古籍整理后继有人。
随着古籍出版数量的迅速增长,古籍出版工作的布局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除原来的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外,八十年代以来,各地先后建立了本省市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如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的古籍出版社,河南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山东的齐鲁书社,湖南的岳麓书社,四川的巴蜀书社,陕西的三秦出版社,安徽的黄山书社,辽宁的辽沈书社,北京的中医古籍出版社等,书目文献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古籍整理和影印本;各地古籍书店及高校出版社、省级人民出版社等也承担了一部分古籍整理出版任务。全国总计出版古籍的单位上百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2 规模宏富,精品倍出
2.1古籍出版物数量倍增
从1982年到1990年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约4000种,约等于1949年出版古籍总数的两倍。
据粗略统计,1982年全国古籍新版书的总数为231种,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57年,此后,历年出版种数不断上升。1983年为281种,1984处为375种,1985年为523种,1986年为541种,1987年为562种,1988年为475种,1989年为506种。
2.2 古籍出版物品种繁多
2.2.1 字典类:《中华大典》——我国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出版工程。这部 新型巨书,于1990年5月开始编篡,所集资料起自先秦止于1911年辛亥革命,初步计算约为7亿字,收书两三万种,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为了保证《中华大典》的编篡质量,国务院要求“集中一批专家和学者,充分依靠和发挥他们在编篡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得到了老一辈有声望的专家和学者的支持,如:胡乔木,钱钟书,冯友兰,钱学森等,他们多从决策的高度,对编篡《中华大典》的意义、指导思想、编篡方针、框架结构、实施方案等方面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谈了各自的见解。
《中华大典》包罗百科,内容广博,学术性强,规模宏大,包含“典”21个,“分典”96个。它的经目从上至下分为四级,即典、分典、总部、部;纬目依次据题解、论说、综述、传记、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9项展开。
另外一部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工具书是《殷墟甲骨刻辞类篡》,该书在编纂上以文字形体为主要线索,以辞条为基本单位,结合辞条内容,对现已发表的全部殷墟甲骨刻辞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共采用甲骨5万片左右,分部首149个,列字关3400多个,辞近2000万条。每辞都据原篆摹写,并附释文,吸收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此书既是殷墟甲骨刻辞的分类汇编和通检索引,也是具有较好学术价值的研究考释成果。
2.2.2 全集、选集
近年来,全集、选集的出版比较频繁。《全宋文》已由巴蜀出版社1988年6月开始陆续出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建安七子集》、《陆云集》、《李商隐诗歌集解》等都已上市。
2.2.3 诗文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等都已先后出版了。
2.2.4 民族古籍
1987至1997年十年间,我国共整理民族古籍书目11万多种,出版民族古籍3000余种,已初步形成一个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体系。在整理出版民簇古籍时,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坚持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把握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2.3 大部头丛书层出不穷
近年来,古籍出版与整理已逐步走向规模化、多卷化的方向。
在第六十二届国际图联大会和第六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传世藏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是由北大教授季羡林担冈主编,诚成企业集团策划并全额投资,海南国际新闻中心出版,全书共123册,1991年启动,1996年8月完成编纂,全书共收书1000余种,30000多卷,书共计2.76亿字。
还有由全国专家学者整理编纂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前者经过普查,汇集分藏于海峡两岸200多个图书馆及散落在美、欧、日等地的全部现存四库存目中的历代典籍4000余种、60000余卷,按经、史、子、集编排,分装1200册全套精装豪华本出版,包括乾隆以前中国历代典籍,《续修四库全书》是继十八世纪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之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也是对乾隆后辛亥革命近二百年间学术文化发展的一次归纳总结。全书共收书5000种,分装1800册一套出版。这两项浩大工程完成后与《四库全书》配套,将构成一座中国基本古籍的大型书库,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建设中,树立中华文苑一丰碑。
3.适应时代,面向大众
3.1白话本、今译本
从目前中国的古籍图书市场来看,我国古籍出版白话化趋势已形成。海峡两岸已有不少学者,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找到了古籍赢得读者的有效途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古籍白话化”。台湾的蔡志忠先生把诸子中的庄子、孙子、老子等以及《史记》、《四书》等搬上漫画舞台。改革出版社也出版了白话文《资治通鉴》,贵州人民出版社今译了《四书》、《今古文尚书》等几十种古籍。
3.2 古籍出版走向大众化(简体、横排)
随着古籍出版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古籍采用简体字版式横排方式,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如1997年初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跨世纪文化工程——《新世纪万有文库》,全部都是采用简体横排,以其中所收之书便可窥其端倪。《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礼记》、《春秋左传》、《文史通义》、《书林清话》、《史通》、《孔子家语》、《荀子》、《梦溪笔谈》等书都是采用简体横排。
3.3 古籍整理走向电子化
3.3.1 古籍数据库的建立
利用计算机整理中国古籍,是近年来研究的新课题,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研究所已经开始了用电脑编纂《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的试验,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也在用电脑储存古籍,校勘古籍,同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在编纂《中国古籍总目》的基础上筹建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3.3.2 电子版《四库全书》的出现
湖南华天集团、湖南电子音象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了全文检索电子光盘版《四库全书》及其排印本,电子版《四库全书》具有以下特点:全文录入,有全文字库和编码方案,易于查找和全文检索,采用多级结构参数化曲线字库技术,其文字可无级放大缩小,阅读时清晰爽目;提供十万字的在线电子字典和词典,可使难懂字词在线帮助下解释、注音,使读者都可读懂,并可任意摘录打印。
电子版《四库全书》的出版,为我国传播传统文化,实现古籍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为我国古籍推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4.目前古籍出版的不足之处
4.1 白话点校、注释、翻译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有些出版社不问古书的内容,大搞翻译;许多古书的注释、点校错误百出,误导读者;有些明明不是全译的,也打着全译的招牌,炒来炒去,有些人从中谋取了不少好处,而对于古籍阅读的普及,则收效甚微,甚至帮了倒忙。另外,选择某些值得普及的古书译成白话是可以的,如《史记》、记传类的书尽可译成白话,但如《律书》、《天官书》等,不但不易翻译,译出来也很少用处,需要的专家尽可读原文,不用白话本,且对一般读者也无多大意义。
4.2 管理混乱:有些宣传封建迷信的糟粕,也打着“开发古籍”的名义出版了,给图书市场的管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对于宣扬封建迷信的古籍,应采取措施,禁止其出版。
4.3 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技术手段问题:在整理和研究古籍方面,电脑的应用不够。这些年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和高校委员会都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甚微。目前,许多古籍重排时,校对出现的错误实在太多。
4.4 电子化程度不够。目前,虽然《四库全书》已发行电子版,但其它古籍的电子版太少了。要更好地实现古籍信息资源共享,图书电子化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在这一方面,古籍的开发具有很大潜力。
4.5 对人员发挥不足:目前,不论是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队伍,还是从事古籍图书出版的队伍,都有待加强。有些单位在老中青结合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充分调动中、青年专家和学者的积极性,导致了古籍整理工作中的脱节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古籍整理工作述略/潘寅生//图书与情报.—1997.(1).—1—5.
2. 我国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体系初步形成//人民日报(京),1996.5.9(5)
3. 古籍整理出版:成绩很大,问题不少: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楼宇烈先生一席谈/逸如//北京日报(京),1995.5.5.(5)
4.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10年成果展在北京举办/文愉//中国出版年鉴1994.—138
5.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四十年概况/程毅中//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315-317
6. 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收获: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综述/张世林//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317—320
7. 谁创造了文化神话:来自《传世藏书》的启示/慕容文清//中华读书报.—1996.12.4.(1)
|